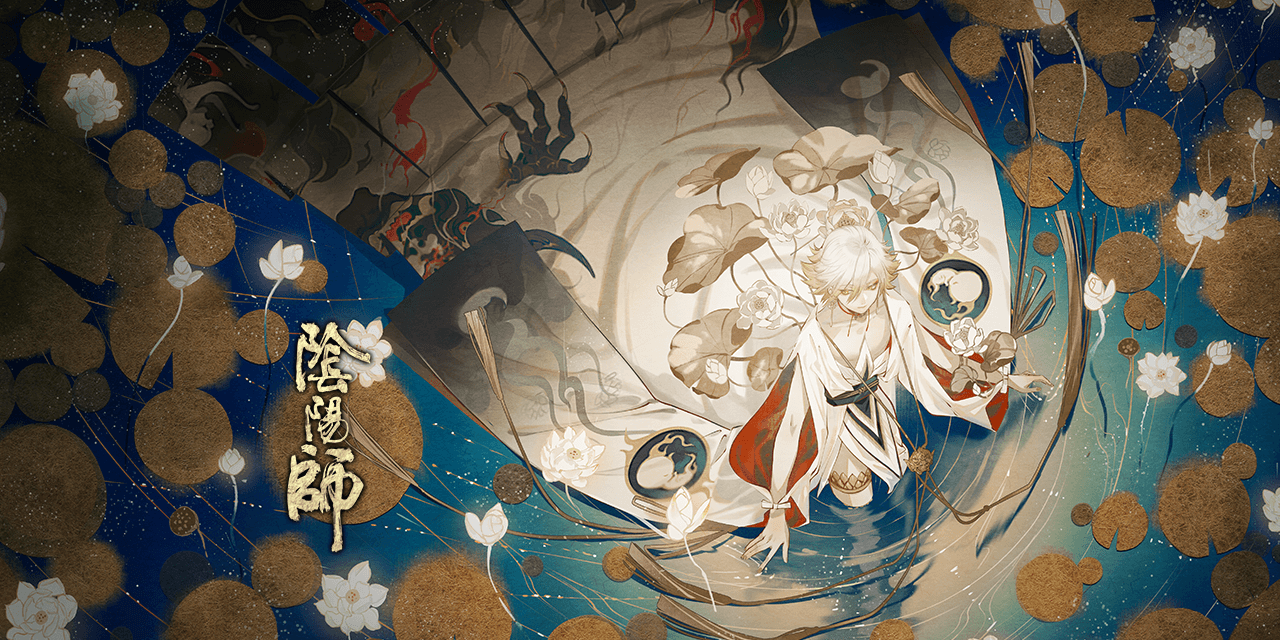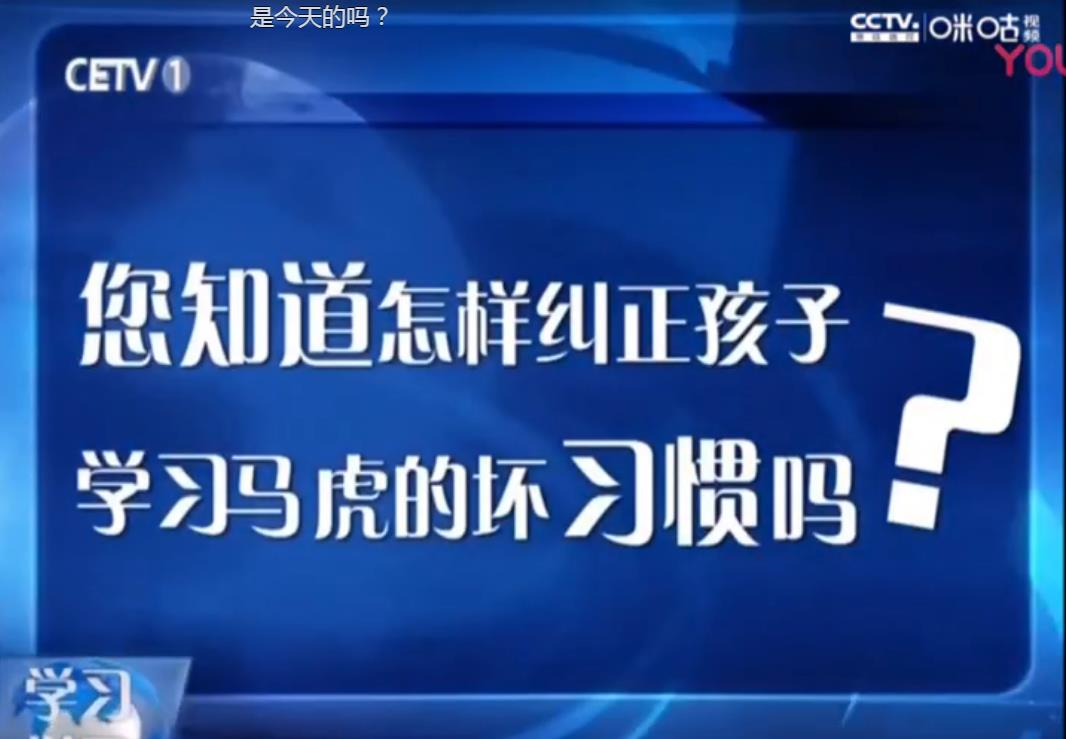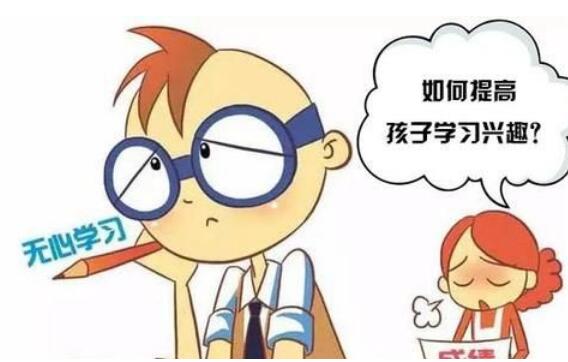(传奇)江上青的诗情、亲情与友情
这让江上清格外感伤。 江上清写的诗中,多次写到了对父亲的怀念,表达了对父亲的无限思念。 蒋世熙刚刚去世时,蒋上清写下了《哭泣的父亲》这首诗。 诗曰:“生时忆朝露,死时辞别近中秋!” “我不能为父亲哭泣,但父亲不知道我儿子病了。” “我想念我的父亲,我的父亲走了,我儿子的心是什么?” “梅花今日薄,泪如年夜诗!”父亲无忧无虑,父亲在睡梦中就去世了! “我从小就被兄弟姐妹围绕着。”那令人心碎的生死离别,被写得淋漓尽致。江上清回忆起父亲优雅的诗书画风对他从小到大的影响。小时候,父亲有威严的一面,但更多的是善良、友善,如沐春风。江上清也觉得,父亲在世的时候,他不需要在生活上有更多的顾虑。父亲去世后,他觉得自己的担子更重了,让他每晚都无法入睡。上清非常喜爱父亲的诗,通过背诵父亲的诗,他不仅提高了自己的诗歌创作技巧,还领略了父亲的精神世界。其中“瘦于梅花,嘲冰雪之寒”这句台词给江上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江上清在后来的悼念父亲的诗中多处提到这首诗。 除《哭父》外,《先父周济之灭》中写道:“除夕夜,吟诵悲愤句,今更知龙头梅”。 《病中吟雪》诗中也写到:“忆父故乡,岁末惊心,谁家瘦病?”
”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出,江上清对父亲的思念、对父爱的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深。断卷英雄对妻子王哲兰最深情的爱是另一个重要的内容。江上清的亲情方面,王哲兰与江上清同岁,原籍上海,是江上清舅舅朱友存的侄女,她经常和江上清的舅舅家一起去。她从小就有父母,所以她从小就认识江上清。 江上清小时候,就跟舅舅朱友存学诗。 王哲兰在扬州的时候,就和江上清一起读书。朱友存聪明、有抱负;王哲兰美丽、有教养,两人从小到大都给彼此留下了难忘的印象,进入高中后,江上清走上了坎坷的道路。江上清的理想和追求常常令人惊讶。 王哲兰虽然不完全理解,但她坚信他做的事是对的,并且一直默默支持。 青梅竹马、青春时的默契让他们越走越近,爱情之花悄然绽放。 1935年9月,江上清与王哲兰携手步入婚姻殿堂。 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,江上清的心情是复杂的:革命低潮的压抑,国事变迁的忧虑。 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孤独感、身体疾病的折磨、父亲去世后家道的衰落等等。不知何去何从,一直萦绕在江上清的心里。 江上清放不开。
尽管如此,江上清和王哲兰的婚姻还是给江上清的生活增添了一些色彩。 王哲兰完全理解丈夫的想法,并尽力安慰江上清。 面对新婚生活和新婚妻子,江上清写下了一首七韵诗《殷赠兰妻思爱》。 在这首诗中,江上清一方面写了《红泪》、《清歌》、《春梦》、《凤鸣》的新婚生活,另一方面写了与妻子“谈风吹雨打”的通宵长话。三点以后下雨”; 一方面,江上清表达了对英雄的看法,认为“破卷英雄最有情”,不陶醉在新婚的喜悦之中。 心中所念、心中所想,依然是志在千里的“豪情万丈”。 江上清经常外出承担学校教学任务,参加各种社会活动。 但一有空,他就和王哲兰一起散步、聊天。 王哲兰怀孕后,江上清刻意多花点时间陪伴王哲兰。 1936年5月的一天,王哲兰怀着第一个孩子已经八个多月了,江上清陪着王哲兰散步,直到走出北城门,参观了扬州著名的施公庙。 随后,江上清写下了《游沙沙·丙子仲春——游梅花岭重格布寺》诗。 诗中,江上清一方面赞扬了石可法的凛然正气,另一方面抒发了逝去岁月和未竟之志的惆怅。 1936年7月,江上清与王哲兰的第一个孩子江泽苓出生。 江上清沉浸在第一次当爸爸的喜悦之中。
与此同时,他也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。 抗战爆发后,蒋上清发起成立江都文化学会救国会(以下简称“文九社”),组织领导江都文化学会救国会流动宣传团(江文集团(以下简称“江文集团”),全心全意致力于抗日救亡事业。 激流中。 没有时间陪伴妻子,尽管他们的孩子还在襁褓中。 1937年11月22日,江上清毅然离开妻女,带领“江文团”踏上宣扬抗日救亡的长途跋涉。 此时,王哲兰已经怀上了第二个孩子。 她多么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一直留在家里,陪伴在自己的身边。 不过,这句话她并没有对江上清说。 因为她理解丈夫的想法,也毫无怨言地支持他的行动。 她只是把对丈夫的爱和依恋深深地埋藏在心里。 面对心爱的妻子和爱女,江上清的心里也充满了难以割舍的感情。 然而,为了抵御敌人和侮辱,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,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,个人和家庭的情感在江上清的情感平衡中不再是最重要的。 革命事业和个人情感并不是不相容的。 工作间隙,江上清时常想起远方的妻女。 想到自己离开多年,家庭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了妻子柔弱的肩膀上,江上清心里充满了愧疚。 尤其是1938年3月,当江上清听说又生了一个女儿时王者兰,心里不由得高兴,另一方面也更加思念妻女。 此时的江上清只能写几句,谈写书,以慰自己对亲人的思念。

同时,在可能的情况下,江上清还把自己微薄的个人零花钱拿出来寄给家人,补贴家里的开支。 1939年6月29日,江上清给王哲兰写了一封家信,内容如下: 哲兰如相见,前书重赏。 海天相距遥远,灵魂与梦想劳作。 两个儿子身体健壮,让他们很高兴。 明天一早我们要去外地小旅行,二十天后回医院。 发十块钱,聊你喜欢的一切。 这封家书的文字很简单,只有寥寥几个字,但对妻女无尽的思念却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书页上,爱意是那么真挚,蕴含着万言千言。 两个月后,江上清怀着对党的事业、民族的伟大事业的无限忠诚,对亲人的无限怀念,倒在了自己追求的理想之路上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这种爱变得更加强烈。 江上清对共同经历生死的战友有着热烈而深厚的阶级友谊。 江上清的许多诗篇都记录了这种浓浓的同志情谊。 新诗《握手·献C·L》和歌词《忆凤台笛·怀民》都描写了江上清与好友罗和民的互动。 罗和民,原名罗家骝,1914年出生于江苏扬州。罗和民虽然比江上清小3岁,但他几乎与江上清同时参加革命,早期的革命经历是非常相似。 他们都于1927年加入共青团,都参加了扬州党组织领导的早期革命活动。 他们双双在1929年的“一月事件”中首次被捕,均被当局判处三个月徒刑。 被关押在苏州监狱。 出狱后,他们都到上海读书。 江上清就读于上海艺术学院,罗和民就读于浦江中学。
在上海,他们同时参加了革命浪潮。 罗和民任共青团上海市湖西区委员会组织部长。 后在上海被敌人逮捕。 抗战爆发前后,罗和民从事进步文化工作。 1931年,蒋上清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,参加党领导的学生运动。 一次活动中,江上清与罗鹤敏意外相遇。 《握手-礼物C·L》(C·L是“小洛”拼音的第一个字母)记录了在异国他乡遇见老朋友的情景和感受。 刚见面的那一刻:当我的目光落在你的头和脚上时,我的整个人就出现在你的面前。 在那闪电般的目光交汇的瞬间,我们不自觉地伸出了有力的双手,同时,向前迈出了一步,我们紧紧握手。 那些在扬州城里一起战斗的战友,那些被关押在敌人监狱里的战友,那些历经磨难继续追求美好未来的战友,在异国他乡、同一个战场上重逢。 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,对于两个无所畏惧的年轻人来说,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。 一次长途旅行中的相遇。 所以,当他们不期而遇的时候,他们就没有再多说什么。 他们都深知对方肩负的重大责任,也都感受到了共同的使命。 相互之间,不再对视,两个人体内的血液交换,从指尖到全身,深入到每一条运转的血管中。 我们的脸上没有笑容,没有喜悦,没有悲哀(传奇)江上青的诗情、亲情与友情,但夹杂着生命的热度。 什么也没说,沉默中蕴含着无限的言语,过去、现在和未来都包含在坚定、坚定、亲切的长握手中。
在风雨飘摇的白色恐怖中,在快节奏、紧张的工作中,他突然遇到了一位早年的挚友。 江上清心中油然而生一种喜悦之情,一种难得的快感。 我放下双手,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这呼吸已经让我窒息了两年,从来没有舒畅过。 江上清另一首思念战友罗和民的诗是1935年春写的《凤台忆笛·怀民》。当时江上清在江苏东海(现连云港)人民教育馆工作。 。 由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,江上清如孤雁,心情郁闷。 于是,“人愈消瘦”、“孤独愈加悲伤”。 收到罗和民的信后,江上清回忆起自己与罗和民打架的经历,但现在“被重重束缚在马厩里”,不免“消磨饮恨,终日愁眉苦脸”。 我有很多话想对战友说,但“远道难言”、“无言以达泪”。 尽管如此,江上清仍然对未来充满希望,“除忧外加,盼春去秋来”。 罗和民的革命生涯中,曾七次被捕,遭受敌人酷刑,但他的革命信念始终不渝。 1947年参与党领导的进步刊物《文萃》的出版印刷。 同年7月,被敌人逮捕。 1948年12月27日下午在南京被敌人杀害,是著名的“文崔三烈士”之一。 陈苏是江上清弟弟江树峰的同学,后来也成为了江上清的好朋友。 陈苏有进步的思想和拼搏的精神。
当他在扬州中学读初中时,陈苏、姜树峰等人发起“直升运动”,要求该校初中毕业生考试合格后直接进入该校高中。 遭到学校反对后,陈苏、江树峰等人联合学生发起“罢课”。 迫于压力,学校最终同意学生直升,但解雇了领导直升运动的陈苏、姜树峰等人。 陈苏被扬州中学开除后,搬到与扬州隔江相望的镇江继续读书。 在镇江中学读书期间,陈苏积极参加“9月18日”、“12月28日”抗日救亡运动,再次被学校开除。 陈苏移居上海求学,就读于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和光华大学。 在上海,陈苏参加了“左翼联盟”领导的进步文化运动,并在《申报》、《时事》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批评时事弊端。 1935年秋,陈肃赴日本留学,在日本明治大学攻读历史学。 陈君业也曾随陈苏赴日本留学。 陈俊业是扬州人,是江上清的好朋友。 陈君野,1914年出生,就读于上海震旦大学,中国进步作家组织“左翼联盟”闸北支部成员。 1932年,他与蒋上清等在扬州创办进步刊物《新世纪周刊》,宣传抗日救亡运动。 然而《新世纪周刊》创刊不久就被当局查封。 陈君业在扬州无法立足,便去了上海。 在《申报》“自由谈话”栏目发表多篇犀利文章,主编大型文学杂志《春光》。 他曾在本刊上发起过一场关于“为什么中国目前不出伟大作品”的大讨论。

《春光》第一至三期发表了许多思想进步、影响广泛的文学作品。 艾青的成名作、长诗《大雁河——我的保姆》原发表于《春光》。 由于《春光》的进步性,该刊在第四期出版前就受到反动当局的干扰,被迫停刊。 不久,陈君业赴日本留学。 大约半年后,从日本传来不幸的消息,陈君业因肺结核去世。 1936年春,陈肃从日本回到扬州,从日本带回了陈君业的骨灰。 江上清得知陈君业去世的消息。 他悲痛欲绝,写下了《鹧鸪天·悼君夜》诗。 诗曰: 思往事,朦朦胧胧梦:广陵才子闲谈时。 茫茫蓝色的悲伤海洋中,痕迹瞬间化为灰烬。 此次陈苏返回扬州,江上清和另一位好友庄守慈陪同陈苏夫妇游览了扬州著名的瘦西湖。 江上清写下《一剑眉·丙子中春与素凤夫妇寿词游瘦西湖》诗,以纪念此事。 从这首诗中,我们可以看出江上清与陈苏之间的真挚友谊。 诗中有一句:“昨日思乡,明日分离”。 意思是不久前,我的朋友在异国他乡,想念家乡和家乡的亲人朋友; 回家后,很快就要离开,更增添了依依不舍的感觉。 离别悲伤。 抗战爆发前,陈苏完成了日本学业,回到扬州。 不久,江上清、陈苏等人发起成立“江都文化圈救亡会”,后来在此基础上成立了“江文化集团”。
江上清和陈苏都是“江文团”的主要领导成员,领导了半年多的长途流动宣传活动。 参加武汉保卫战后,陈肃病重,于1938年10月上旬落水身亡。 罗家骝、陈苏、陈俊业等都是有才华、有理想的进步青年。 江上清和他们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文学上都有着相同的追求。 可以说,他们紧密相连,目标相同。 不过,江上清的朋友并不仅限于此。 只要是有学识、互相尊重的人,无论年龄大小、等级高低,江上清都会和大家成为朋友。 在广泛的交往中,江上清不仅用朋友的长处弥补了自己的不足,也赢得了朋友的尊重。 张玉平,1878年生,清末人。 他在文字学、音韵学方面造诣颇深,着有《江都方言讲解》。 虽然张玉萍比江上清大了二十多岁,但江上清却与张玉萍交往频繁。 江上清经常向张玉萍请教相关文字学知识。 有一次,江上清问张玉萍“魁”字有没有几种解释,是否是“轿”的意思。 张玉萍说,没有。 江上清说,这个词出现在《开明文选》和《无双传》中,注释是“轿”,是用竹头写的。 张玉萍说,这是假话。 后来,张玉平查阅唐代丛书《刘无双传》,澄清“奎”误为“篼”,“篼”是“轿”的意思。 张玉平还专门写了一张纸条,告诉江上清他查到的文字的意思。 孙香谷是1935年下半年江上清在扬州平民中学任教时的同事,两人住在一个房间。
孙象谷虽然年纪大了很多,但蒋上清的谦虚好学赢得了孙象谷的好感。 教学结束后,江上清与孙香谷谈诗论文,探讨教学方法,两人的友谊越来越深厚。 孙相谷曾赠诗一首江上清:“漂流相逢欢喜,篝火触膝填满心,久善画花画笔,隔崖仰望群峰,大地与文才深议,闺阁自在相争。” 年轻时,他有很多泥爪,不惜用较浓的墨作画。 ”江上清回复了一首《不孙张相谷辞云》诗。诗中说,由于一种缘分,老少共处一室,谈诗作词,成为知己。江上清很珍惜这份友谊。诗的最后写道:“幸好我追随继伟到了扫牙,天涯兄弟成了老沿江树峰,原名江世波”。出生于1914年,当时小江上清3岁,他既是江上清的弟弟,又是他的战友,在多年的并肩战斗中,两人结下了特殊而深厚的友谊。兄弟中最小,江上清称他为“七哥”,从小就受到江上清的影响,他机警好学,追求上进,大三的时候就加入了青年团。就读于扬州中学。 初中即将毕业时,他因发起“直升运动”而被学校开除。 后转入上海公学。 1933年至1936年,蒋树峰先后在天长中学、镇江崇实中学、扬州平民中学任教。 他和江上清都是平民中学的进步青年教师。 1935年下半年江上清写的《不孙张香谷词韵》诗中,有“江南江北仰戴凤”之句。 “戴风”指的是江树风,表达了当时江上清与扬州的关系。 我想念在江对岸的镇江教书的七哥。
1936年下半年,蒋树峰参与了蒋上清等人发起和领导的进步刊物《写作与阅读》的编辑出版,并积极为该刊物撰稿。 该杂志第一卷出版时,树峰正在镇江任教。 当时,《写与读》的另一位创始人于在春也在镇江,负责第一卷的审阅和印刷。 不过,由于于在春病愈不久,邮寄、校对、印刷等许多编辑工作都是在姜树峰的协助下完成的。 1937年8月,蒋树峰参加了蒋上清等人发起并领导的江都县文化圈救亡会。 11月,还参加江都县文化圈救亡会流动宣传队。 江树峰和江上清一起踏遍山河,宣传抗日救亡。 江树峰和六弟江上清一起战斗,一起生活,互相扶持。 江上清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给江树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对江树峰的成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 姜树峰在“姜文团”中担任海报组组长,成为“姜文团”的骨干成员。 1938年8月,根据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的指示,“蒋文团”成员被分配到新的工作岗位。 江上清去了皖东北,江树峰则被分配到了广西。 在武汉浠水分道扬镳时,江树峰和江上清惺惺相惜,难舍难分。 江树枫和江上清分手后,虽然身在异地,紧张地忙碌着,但彼此通过书信保持着联系,还经常互赠诗词。 江上清经常评论七弟的诗。 1939年8月,江树峰收到了江上清的信。
信中称“哥哥的诗文有了很大的进步”,并寄回一首诗给江树枫,这就是齐鲁《致七弟江树枫》。 诗句“春水青杨思故乡,秋山红叶在路,天涯兄弟已长大,问老病老”。 深情地表达了江上清对家乡、对亲人、对七弟的无限思念。 让江树枫万万没想到的是,这竟然是六哥的最后一部作品。 江上清对家人和战友的深厚感情,和江上清对革命的坚定追求,共同构成了江上清烈士丰富多彩的一生。
阴阳师4月22日更新内容:帝释天上线技能调整,红莲华冕活动来袭[多图],阴阳师4月22日更新的内容有哪些?版本更新
2024-05-06四川电视台经济频道如何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与方法直播在哪看?直播视频回放地址[多图],2021四川电视台经济频
2024-05-06湖北电视台生活频道如何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直播回放在哪看?直播视频回放地址入口[多图],湖北电视台生活频道
2024-05-06